
年末的一个傍晚,一场倾盆大雨在布依(Bờ Y)边境地区下着,淋浴着山林万物。此地的寒冷和寒风也与众不同。沿着长满青苔的台阶,我爬到了山顶。这里竖立划分三国边界主权的界碑。我们常把这块界碑叫成“印度支那丁字路口”。
在海拔1086米高处上的界碑,朝着三国远望去两公里以上的距离,只是山峦起伏。朝着越南的是崑嵩省,朝着老挝的是阿速坡省,朝着柬埔寨的是腊塔纳基里省。
你只要绕着这块界碑走一圈,就踏上三国的领土,真是世所罕见的。花草树木虽然在一块,但是色彩斑斓。
谈到西原时,就想到高原上的山峰。

嘉莱省朱登亚火山。(图片来源:越南旅游总局)
嘉莱省朱登亚火山。(图片来源:越南旅游总局)
我在大雨中所站的地方不是有名山峰,而是一个高度相对的山丘,不过这是一个神圣之地。
界碑是见证卫国战争和国土扩张历程之地,游客可在此地易于体会到西原的内涵与形象。
谈到西原时,就想到高原上的山峰。
从山顶上,雨越下越大,烟雾在树林里缭绕。空间在眼前朦胧,这一边是我国山脉,那两边是柬、老两国森林。这种景色仅增进隐藏着对偏僻山区的怀念的寂寞。
从这个“印度支那丁字路口”,我朝着阳光向西原远望着。在感受体验中,不由想起对我国既奥妙无穷又格外亲切的思念。
这里的山脉、河溪是展现鬼斧神工的自然之美。西原同胞认为,山越高、河越深、瀑布越多,许愿会越灵验啊。
当地居民根据山河之音行动起来,山脉、河溪的魂魄也渗透此地山区民众的血管,并形成明哲体系。
山峰、大河是信仰的空间,是浪漫的故事。
西原山河不仅隐藏地理指引,而且还是我国神圣魂魄的一部分。

橡胶种植基地在居民小区里发黄。
橡胶种植基地在居民小区里发黄。
巍然屹立的朱昂新(Chư Yăng Sin)、碧多(Bidoúp)、玉灵三大山脉是大森林中三个屋脊,形成一个牢固的三鼎足,是精神坚强且无比自豪的形象。
克隆奴(Krông Nô)、克隆阿娜(Krông Ana)、斯雷博河(Sêrêpốk)、色桑(Sê San)、同奈等大河的发源地在高山,像彩条一样地穿过森林和村寨,隐藏着许多历史文化的沉积与价值。
从荒芜山野、从背靠山面向江的那些村寨而《达姆伞》(Đam San)、《生雅》(Xing Nhã)、《轻俞》(音译Khinh Dú)、《东余》(音译Dyông Dư)、《登内》(音译Đăm Noi)等史诗问世。

西原锣钲舞。(图片来源:《人民报》)
西原锣钲舞。(图片来源:《人民报》)
从山石,林竹而锣、钲、石琴(lúrgòong)、汀宁琴(tingning)、特龙琴(klôngpút)、绍竹琴(t’rưng)等乐器已奏响神奇的声音。
《泥》(Nrĩ)、《泞》(Nrìng)等民谣;《哎雷》(Ayray)、《库特》(Kưứt)、《啦珑》(音译Lảhlông)、《牙瑶》(音译Yalyău)等民歌;夜间在森林里的火炉边,民舞节奏与人心融为一体,空间如梦如实。



多少年穿越这片茂密的森林,我总在询问自己,西原的内涵是由哪些具体的特定图像来定位和测量的?
基于高山水深,神秘的森林,辽阔的草原,深厚的文化价值还是数百万年形成的沉积石?
果真 ,难以用现有图像来量化。高山低山,大河小河皆有上游之源。该山区的村寨几乎都有共同的根源。
我在Núp英雄的Stơr村寨,乔治·孔多米纳斯(G. Condominas)找出石琴和撰写《我们吃了森林》一书的Salúk村寨,坚忠的斯丁族的Bờxaluxiêng区,埃地族崇拜源头的水滴之地的Kotam村寨还是布娄族的Đắk Mế区等都具有相同的简朴、友好的色彩。

嘉莱省Đê K'Tu村寨。(图片来源:旅游总局)
嘉莱省Đê K'Tu村寨。(图片来源:旅游总局)
我游过的村寨都有山脉森林呵护,河流滋养生命,人与山势河流相融相生并建造长存的文化价值体系。
在该上游地区的民族,诸如布娄族、勒曼族等人口较少的民族,还是埃地族、巴拿族等人口多的民族都有共同语言,居住空间,共同节奏以及高原的神圣爱火。

在传统龙屋(Nha Rong)前。(图片来源:人民报)
在传统龙屋(Nha Rong)前。(图片来源:人民报)
西原,永远是梦幻之地。
在雄伟的长山山脉脚下,各兄弟民族携手并肩谱写这片骄傲土地的历史。
在雄伟的长山山脉脚下,各兄弟民族携手并肩谱写这片骄傲土地的历史。
那就是穿越千年建造和培育的闪亮的记忆。
那就是在各场保卫国家长征中如山如水坚心守志。
那就是穿越千年建造和培育的闪亮的记忆。
那就是在各场保卫国家征程中如山如水坚心守志。
从荒芜,从血与火中,西原人民世世代代面临困难重重和无数的敌人,但是他们都战胜并确立了森林主人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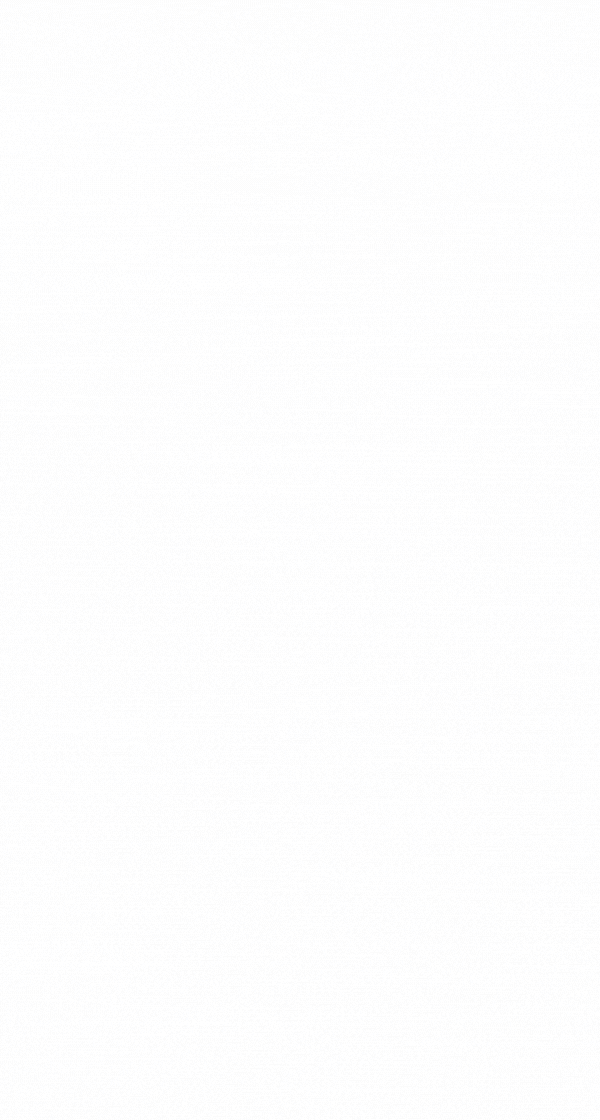
了解西原了没有?每次问自己这句话,我不禁想起了法国著名民族学家雅克·杜恩斯(Jacques Dournes),几乎一生沉浸在西原文化之中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必须理解才可以爱,那么必须爱才可以理解”。
雅克·杜恩斯第一次来西原就居住了近10年,作为一名传教士却热爱研究文化而忘记任务,因此1954年被召回法国。
雅克·杜恩斯第二次重返西原已居住了10多年,此次他是真正的一名民族主义者,直至1970年被迫离开越南。
雅克·杜恩斯用自己四分之一人生在杰林(Djiring)高原上与格贺族人民和巴江下游区域的加涞族人一起生活。
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西原,西原文化却征服了他。这位牧师变更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追随同胞的信仰,放弃教理而寻找文化源泉。

浪平山脚下的格贺族姑娘。(图片来源:人民报)
浪平山脚下的格贺族姑娘。(图片来源:人民报)
从深林、梯田和高脚屋的火炉,雅克·杜恩斯创造出伟大的研究著作,为寻求西原民族学的人打下基础。
雅克·杜恩斯的作品是这位人类学家在征服西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西原征服了他的过程中留下的研究项目典范。

维护和弘扬西原文化之美。(图片来源:人民报)
维护和弘扬西原文化之美。(图片来源:人民报)
谈及雅克·杜恩斯的故事就明白,西原是如此具有奇异魅力之地。
我不敢和雅克·杜恩斯民族学家相比,我只是一个有机会“游过梦幻的西原”的普通人,却对这片土地情深厚爱,我以为爱上了就会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一天晚上,在录北林中的长屋里,麻族村的村长卡叶(K’Diệp)把我拉到火炉边,在我的额头上滴了几滴鸡鲜血,并祈求神灵为村里见证收容一名京族男人为子。

麻族艺人乡青年一代传授传统音乐。(图片来源:人民报)
麻族艺人乡青年一代传授传统音乐。(图片来源:人民报)
在莫名的感慨中,我突然发现自己对西原一无所知。 被领养为大森林的孩子是一种荣幸,但这就像一个新的开始。 旅人为了自己的爱情从 “a、b、c...”最初开始摸索着。
西原内涵会以什么形象来量度?
那个下着雨的午后回到三国边界的山林一角。在前线站与我交谈的是来自崑嵩省的叶坚族同胞阿雄大尉和清化省芒族一等兵围文僥。
这时候,当我谈起保家卫国者的神圣使命,谈起昔日英雄阿生在博果(Po Co)江上带兵出征的独木舟的记忆时,我感受到,西原内涵是以边防部队热爱祖国之心来衡量的。
同一天下午,我和九十多岁的伊潘(Y Pan)村长坐在了一起,他是布娄族得米(Dak Me)村女村长。

麻族人的传统长屋。(图片来源:人民报)
麻族人的传统长屋。(图片来源:人民报)
伊潘老人给我讲了她的民族,一个只有322人的民族的生存和文化故事,比森林树上的叶子数量还少。
原来,西原内涵是最具体、最简单且最神圣的。 它是边疆地标,是森林中的古树,是祖国山脚下的巉岩,是坚持不懈守护民族文化的人,是以生命为界标守护祖国家乡每一寸土地的勇敢战士等等。

我也明白,西原的梦幻,远在数百万年前造就了高山深水,创造了壮丽的史诗,诉说了祖国波澜壮阔的过去。
而且,西原的梦幻,也就像我每天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遇到的人一样亲近和熟悉。(完)



